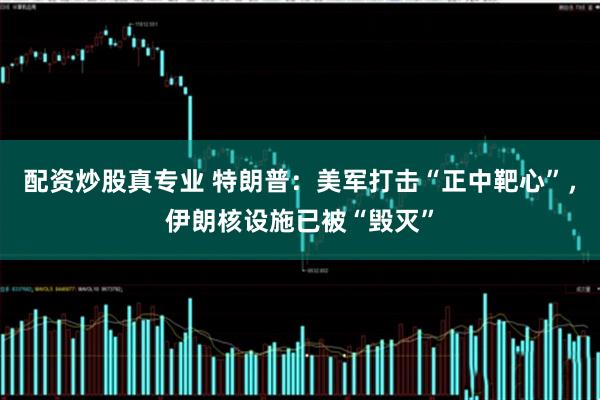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江晓博/文线上配资平台官网
图片
【知远导读】美军的联合后勤有其特殊性,比如灵活的联合后勤控制方式、独立的运输司令部、统管通用物资的国防后勤局等,这一特殊性源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战争实践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本文从历史角度,简要回顾了美军联合后勤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美军不断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推动联合后勤前进的过程,以期为读者提供更加清晰的历史脉络。
我们当前看到的美军联合后勤,其实是联合后勤比较高级的形态,并不是生来就如此。联合后勤自诞生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那么,它到底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本文将一探究竟。
一、后勤是必然要走向联合吗?
当你第一眼看到“联合后勤”这个词,有没有产生过一个疑问:为什么“联合”能与“后勤”组合在一起,联合是后勤发展的必然吗?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二战时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他可能会怀疑你的动机——你是不是要削弱海军的权力;如果把问题抛给二战时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他们会觉得你可能在为海军谋取利益。那么,后勤为什么最终走向了联合?可能有两个主要推动因素。
1.资源的有限性
资源的有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总体资源的有限性。比如乌克兰,在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国防预算资金只占其GDP的1%,而战争爆发后的2014-2017年,这一数值也一直在3%左右。如果投入再多,不但乌克兰的经济难以承受,其他涉及国计民生的支出也将受影响,继而造成国内更大的动荡。即便像美国这样全球军费最高的国家,各军种也都为争夺有限的国防预算而费尽心机。二是局部资源的有限性。即便总体资源相对充足,但限于当时的作战环境,也会导致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资源短缺。比如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在东北储备的棉衣、棉帽、手套、给养等御寒物资是不缺的,但由于入朝时间紧迫加上美机对供应线的连续袭扰破坏,导致志愿军九兵团在战前物资储备不足。假如当时志愿军拥有一定的制空能力或空运空投能力,这种后勤资源短缺问题就可以很快解决。因此,资源的有限性是推动后勤向联合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因。可能有人又要问,资源的有限性也不是晚近才出现的,从古至今就有,为什么二战以后才提出联合后勤呢?这就涉及第二个推动因素。
2.联合作战的出现和发展
联合作战的出现为后勤问题提供了联合解决方案。这里简要回顾下联合作战的出现和发展。按照美军早期的定义(1985年),联合作战是美国武装部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军种实施的作战行动。既然陆海军乃至空军在二战前就有,那为什么二战之前没有出现联合作战呢?以下列举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在观念上,二战之前许多军事领导人和战略家仍然持有一种“各自为战”的观念。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军种最为重要,而其他军种只是辅助角色。这种观念阻碍了跨军种合作的深入发展。第二,各国的军事组织和指挥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联合作战模式。例如,在德国,尽管空军(Luftwaffe)在1935年成为独立军种,并且其领导层对战略轰炸和其他任务表现出兴趣,但海军和空军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合作意愿。同样,在意大利,所谓的最高指挥部(Commando Supremo)对各军种没有实际的控制权。1第三,军种竞争阻碍了联合作战的发展。无论是二战时的美国还是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拥有各自的强大利益,尤其是日本,完全没有联合高级指挥机构(直到1944年初才有所改变),除了天皇就没有人能协调陆海军的矛盾,更不用谈联合作战。第四,通信技术也是一个限制因素。有效的联合作战需要高度发达的通信系统来保证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准确理解。在二战之前,通信技术尚未达到能够支持大规模、多军种协同作战的水平。
美国是最早发展出联合作战的国家,其在二战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已初见端倪,其后又在不断的战争实践中迭代和完善,其主要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军种力量整合阶段(二战后至1986年),该阶段美军正式设立了参联会、联合参谋部、地理区司令部以及军种组成部队等,形成了名义上的联合组织架构,但军种主导仍然是此时联合的本质,军种参谋长仍可利用自身权力架空联合机构。二是作战司令部主导的联合作战阶段(1986年至2012年)。1986年的《戈-尼国防改组法案》真正实现了军政、军令分离,真正克服了军种山头主义,尤其是确立了战区作战司令部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三是全球一体化联合作战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美军首次提出“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联合不再局限于地理区域,而是以跨域协同为指导,试图打破战区、领域、层级和部门之间的界限,标志着联合作战进入全新阶段。
伴随以上联合作战的出现和发展,联合后勤也应运而生,并在1995年出现了首部《联合后勤》条令,后续又提出了“聚焦后勤”“全球一体化后勤”“联合对抗性后勤”等联合后勤概念。
二、联合后勤面临的几个现实问题
在回顾历史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联合后勤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真正推动后勤改革前进的是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以下初步梳理了四个方面。
1.联合后勤指挥与控制问题
后勤指挥问题最核心的是资源的分配权,也就是谁拥有资源的最终裁决权。比如,二战时美军的资源分配权在军种部长手中,海军作战部部长有权决定是向太平洋战场还是欧洲战场投入更多的舰船资源。而到了1986年《戈-尼国防改组法案》颁布之后,战区作战指挥官拥有法律赋予的“后勤指令权”,也就是对战区内的资源分配拥有最终裁决权。这一权力掌握在作战指挥官手中,就避免了战区内各军种相互争夺有限资源的情况。
然而,作战指挥官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他需要委派下属部门来代为行使该权力,因此又延申出后勤控制问题,比如后勤控制方式、后勤指挥关系等。例如,在印太司令部,美军既可以指派太平洋陆军第8战区保障司令部充当联合后勤控制机构,也可以通过扩充印太司令部的联合参谋部后勤部来实现联合后勤控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虽然可以代替战区作战指挥官行使“后勤指令权”,但最终裁决权仍在作战指挥官手中,也就是说“后勤指令权”是不能转移的,是作战指挥官固有的。
另外,关于后勤指挥关系,这主要是针对施援单位和受援单位而言的,其核心仍然是资源的分配权问题。比如,美陆军步兵旅战斗队旅支援营的前方支援连,与对应的步兵营之间是直接支援关系,也就是说步兵营营长对该连的后勤资源拥有分配权;而旅支援营的配送连与步兵营之间是全般支援关系,步兵营长无权分配配送连的资源。以上还只是陆军内部的,联合后勤层面将涉及多个军种和部门乃至多国的资源分配问题,将更加复杂。
2.联合后勤计划问题
联合后勤计划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纳入联合作战计划”。比如,指挥官是否在作战筹划之初,就将联合后勤因素纳入其中;后勤计划过程是否在联合作战计划流程中;后勤方面的限制是否会影响联合作战计划的制定;各军种组成部队是否仍独立制定各自的后勤计划而缺乏协同等。例如,在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萨沃岛海战期间,由弗莱彻率领的美军航母特遣队因误判战场形势,放弃了对登岛地面部队的保护并撤离瓜岛海域,使停泊在海湾的美军运输船成了案板上的鱼肉。另外,在岸滩物资卸载过程中,虽然海军陆战队急需这些物资,但由于计划不周、协调不畅,只有海军岸滩勤务队和海军船员在通宵卸货,而附近的1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却在棕榈树下吃椰子,导致大量物资堆积在海滩。
3.大宗物资、通用物资管理问题
大宗物资的采购和管理一直是萦绕在美军头上的大问题。二战时,军队对弹药和油料的需求非常大,美军采取了什么方式呢?当时,美国陆军和海军分别在工厂设立了办公室,各自管理大宗物资的供应链,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竞争,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国防部长威尔逊为跨军种的单个物资设立了一名主管,他可以确定国防部的总需求,然后再从一个军种采购、存储和分配库存。1961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又创建了国防供应局,也就是国防后勤局的前身,将通用物资的采购和管理进一步从军种剥离出来。通用物资的管理问题本质上是军种利益的平衡。
4.联合配送问题
联合配送问题是较晚才出现的,之所以成为突出矛盾,主要是由于美军后勤保障方式出现的变革,即基于配送的后勤模式。战区配送问题关注的是如何统筹战区内有限的运力资源,并使其发挥最大的效能,具体问题包括:如何安排运输优先级,部队普遍倾向于将自己的物资运输需求排在前面,导致真正紧急的需求得不到充分考虑;运输成本问题,空运效率虽然是最高的,但其成本是地面运输的10倍,因此后勤配送系统要能够预测适当的物资需求和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资产可视性问题,如果无法追踪到在途物资的有关信息,后勤人员将根本制定不出有效的配送计划;物资配送管理问题,物资抵达战区后,需要重新包装,如果缺乏识别和跟踪工具,这个过程将非常复杂。例如,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由于信息不准确,后勤人员不得不重新清点所有到达战区的集装箱,而后重新进行物资打包。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顾一下美军自越南战争以来联合后勤的大致演变过程。
三、美军几次战争中的联合后勤演变
以下主要梳理了四场战争或军事行动,即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恢复希望”行动和伊拉克战争,它们在美军联合后勤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1.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从1962年持续到1975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62年至1965年,该时期美国主要以军事顾问形式指挥南越政权作战;二是1965-1975年,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由,派出大规模部队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在战争开始之前有两件与后勤相关的事件需要重点交代。一是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确立了国防部长、三个军种部门和国防部的地位。该法案在消除供应领域军种之间的重复和重叠,并为最终创建一个单一的综合供应机构奠定了基础。二是前文提到的国防供应局的成立,它将8个现有的通用物资管理机构合并为4个,并通过减少冗余和统一行动提高了所有军种的效率。这两件事对越南战争期间及之后的联合后勤改革来说是重要的铺垫。
在越南战争期间,后勤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战役层级,即进入越南战区的物资缺乏集中管理,造成了许多供应方面的困难,例如港口过于拥挤、申购出现错误、交货延误和供应会计错误等。此外,在1962年至1965年越南战争的初期阶段,后勤部队数量不足、后勤基地配置不合理、缺乏跟踪机制等原因,导致西贡岸上积压了大量物资。
为解决这一问题,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就指定海军作为组织越南供应系统的行政机构,负责向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提供后勤支持。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军将其责任区划分为四个战术区,其中海军为北战术区内的所有军种提供通用补给,而陆军承担了其余三个区的责任。分散的供应系统导致各军种之间的满意度较低,因为各军种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需求,而怠慢其他军种。陆军没有储备海军和空军所需的许多物资,海、空军也没有储备陆军单位通常使用的物资。
为了解决越南战场缺乏中央机构协调战区保障行动的问题,美军启用第一后勤司令部。经过几年的摸索,该司令部最终负责指挥和控制战区地面部队的所有后勤工作,并被指定为负责战区后勤管理的总部。然而,第一后勤司令部的运作并不成功,在有效管理供应、维修、部署与配送行动方面效率低下。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物资在作战环境范围内的联合后勤可视,没有实现军种之间的统一努力,也没有以快速和精确的方式配送物资。
回顾越南战争中的后勤工作,大部分时间里,美军没有组建整体的战区后勤司令部作为处理后勤事务的中心机构。直到战争快结束时,陆军第一后勤司令部才被指定为负责战区地面部队后勤工作的总部,但由于指控手段较为缺乏,无法实现联合后勤可视,导致保障效率不高。可以说,越南战争使美军初步认识到集中后勤指挥控制的重要性。
2.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发生在1990年,在此之前,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即1986年10月美国正式颁布《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对美军指挥结构进行了彻底变革,并明确国防部长可以通过《美国法典》第10编授权的七个核心能力来管理联合后勤。另外,在1987年,国防部成立了美国运输司令部,以承担了在平时和战时对国防部资产和人员进行战略运输的任务。这两个事件对海湾战争的联合后勤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海湾战争中后勤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沙漠风暴行动初期,大批战斗部队优先进入战区,但未建立相应的后勤基地,导致数千名士兵缺少后勤保障。中央战区司令紧急派帕格尼斯少将管理战区后勤工作,并以临时支援司令部(PSC)的名义为战区制定后勤计划。与此同时,还利用来自迭戈加西亚的四艘陆军预置船只提供的补给和装备,建立初步的后勤基地。在此期间,陆军被指定为粮食、水、散装燃料、地面弹药、兽医服务和坟墓登记的执行机构;海军实行自我保障;空军依托预置在阿曼、巴林的储备预置船保障。
到了1990年12月,军事领导人认识到需要一个正式的后勤指挥和控制部门来管理在战区的大量物资,于是将临时支援司令部指定为正式的第22支援司令部来执行这项任务。作为一种比越南战争中更加集中的后勤指挥机构,第22支援司令部还负责将后勤整合到战区的总体地面行动计划中。
回顾海湾战争的后勤工作,美国军方虽然从越南战争中学到了教训——在冲突期间需要建立一个总部来统管后勤工作,包括港口和机场的控制。但由于优先投送作战兵力所导致的新情况,后勤的统一指挥刚开始是以一个临时机构的形式出现的,主要靠的是帕格尼斯个人的能力和经验。当时,帕格尼斯有三个头衔:东道国事务协调员、中央战区陆军支援司令部司令、战区分管后勤的副司令。他曾自嘲:“在谈判合同时,自己就是最大的顾客。”与越南战争相比,海湾战争还是初步实现了战区后勤统一指挥,而且其组织架构较好地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另外,从1992年开始,国防后勤局采购了93%的战争消耗品,而这一比例在越南战争期间只有50%。
3.索马里“恢复希望行动”
“恢复希望”行动(Operation Restore Hope)是美国领导的多国军事干预行动,旨在应对1990年代初期索马里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行动开始时(1993年),美国迅速向索马里部署了约28000名士兵。美军及其盟友首先控制了主要港口和机场,并逐步扩展控制区域,确保人道主义通道畅通。为保障行动实施,美军专门组建联合特遣部队支援司令部(JTFSC)。在行动的初始阶段,后勤支援是由海军第一部队勤务支援大队(FSSG)提供的,主要利用了海上预置部队(MPF)和肯尼亚的海军预置部队。后续阶段,在陆军部队开始抵达战区后,陆军第13军支援司令部(COSCOM)被指定为联合特遣部队支援司令部的总部。它临时收拢了大量后勤力量,包括第62医疗大队、第593地区支援大队、第7运输队、第240军需营(油料)以及第548补给勤务营。事后看来,联合特遣部队支援司令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是发挥了平衡战区优先事项的能力; 二是提供了单一军种支援无法达到的规模效益;三是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司令部,以便让剩余部队作为主要力量重新部署。
“索马里恢复希望”行动虽然规模小、时间短,但是它为联合后勤指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显示出将后勤行动并入联合行动进行统一指挥的趋势。
4.伊拉克战争
相较于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后勤统一指挥方面进步明显。战前由联合部队陆上组成司令部后勤部和第377战区保障司令部司令组建了战区支援指挥中心,负责管理和协调伊拉克的后勤工作。但新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联合配送问题。之所以会出现配送问题,主要源于美军后勤保障方式的变革。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采取了“基于配送”的后勤保障方式,这与以往“基于储备”的保障区别较大。以配送为基础的后勤,主要通过及时的配送来补充部队的正常消耗,它只在部队保留了较小的库存,以弥补配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暂中断,类似于当今的京东配送模式。而基于储备的后勤,则是传统上按照部队层级,逐级储备补给品,并按梯次供应,往往需要在各级都保留较多的库存。
理论上,如果实施得当,新的配送系统可以减少对后勤资源的占用,提高效益并节约成本。但在实际运用中,在途可视性方面出现了大问题。一是现有的通信基础设施在快节奏的战斗环境中不起作用。各单位太忙于作战行动而不能按照原先的意图使用信息系统。二是各单位的实际行动速度超过了后勤保障速度。当它们所要求的补给品到达计划的分发地点时,部队已经离开了。三是战区稀缺的运输资产,迫使部队副指挥官每天消耗大量精力用于审查和批准运输资产的分配,因为缺少相关程序。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一个关键事实,即战区内没有一个实体负责战场配送工作,更缺少一个清晰的指挥和控制结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运输司令部被指定为配送管理的统管部门,并在战区司令部创建了联合部署与配送行动中心,使其成为单一联络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陆军又通过模块化改革,将后勤指挥控制进一步向战役级集中。同时还压缩保障层级,组建战区持续保障司令部(TSC),承担战区行动中唯一后勤主管的角色;部署远征保障司令部(ESC),从而提高目标战区的指挥控制效率。这些措施使战区联合后勤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四、结语
美军四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充分表明,在战役层面提高后勤指挥的集中度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战役级的后勤指挥部门应当是现役建制机构;必须能指挥和控制整个战区的后勤行动,包括部队部署前的阶段;同时它还应置于联合作战行动的统一指挥之下。就美军而言,各军种都应当具备充当战区联合后勤司令部的能力,并能随战斗部队一同向前部署。
当然,随着美军联合作战进入全球一体化作战,后勤也更加强调“对抗性”的新时期线上配资平台官网,联合后勤的演变将呈现新的趋势。
【1】William Murray. The Evolution of Joint Warfare. 2017, https://apps.dtic.mil/sti/tr/pdf/ADA426537.pdf(平台编辑:黄潇潇)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佳禾资本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